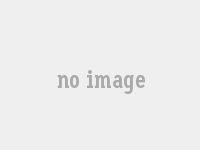律师代理X学校与Y中合同纠纷案
- 案例时间:
- 浏览量:0
- 案例编号:SCLGLD1552357025
- 案例类型:律师代理、辩护成功的诉讼案例
X学校系依法设立并取得办学许可证的营利性民办学校,Y中系巴州区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全额拨款公办学校。2015年8月28日,X学校与Y中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书》,就双方合作办学事宜进行了具体约定,合作办学期限为6年,合作办学范围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合作办学期限内,Y中负责组建合作办学管理团队,行使对X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权,每年向X学校支付校舍、教育教学设施设备使用费600万元。《合作办学协议书》签订后,X学校将学校资产移交Y中管理,并将各年级在校学生交与Y中继续教育,Y中按约向X学校支付了2015-2017两个年度的使用费共计1200万元。
2017年8月25日,Y中以国家政策变化为由,向X学校发函协商解除《合作办学协议书》,X学校认为Y中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不同意解除,并催告Y中按约支付当年度使用费。后因Y中迟迟未支付,X学校于次月向法院起诉,要求Y中支付当年度使用费并支付违约金。
诉讼过程中的2017年11月7日,Y中向X学校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称合作办学后由于国家政策已发生巨大变化,协议已无法履行或不能按预定条件履行,故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及协议约定通知X学校解除《合作办学协议书》。
原审法院判决解除《合作办学协议书》,仅支持了X学校截至合同解除之日的实际使用费共计300万元,X学校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一审法院“所判非所诉”、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案件发回重审后,Y中提起反诉,要求确认《合作办学协议书》于2017年11月7日(即Y中向X学校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解除。X学校委托我所律师代理本案,一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判决支持了Y中的反诉请求即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于2017年11月7日解除,同时判决Y中向X学校支付2017-2018年度使用费共计600万元。
X学校不服一审判决,继续委托我所律师代理其提起上诉,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法院判决之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解除,Y中向X支付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即判决作出时的当学期)使用费共计900万元。
【代理意见】
代理律师做为X学校代理人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我们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双方于2015年8月28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2)Y中所声称的国家法律、政策的变化是否构成《合作办学办学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解除情形或《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3)Y中在诉讼过程中向X学校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力?
一、《合作办学协议书》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且合同性质是普通民事主体之间关于整合教育资源、合作办学的普通民事合同。
X学校和Y中均是依法设立的具有办学资质的独立法人主体,虽然合同一方的Y中是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公立学校,亦不因此改变合同双方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平等地位,《合作办学协议书》的实质就是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整合教育资源、合作办学的普通民事合同。不管是《合作办学协议书》的合同标题,还是纵观整个《合作办学协议书》的内容,双方具体约定了各自在合作办学中的权利义务,涉及招生、师资、学生管理以及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管理等诸多方面,并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租赁”合同关系。
二、《合作办学协议书》自签订以来履行至今,没有出现任何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约定解除情形或法定解除情形。
《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以来,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调整,不但不是禁止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进行合作,反而是提倡两个类型的学校探索多元化的合作模式,这一点在《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就已经明确提出,“积极鼓励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相互购买管理服务、教学资源、科研成果”。因此,X学校和Y中的合作办学,不但没有出现政策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反而恰恰是响应了政策号召。《指导意见》的发文单位是“巴州区教科体局”,其性质是巴中市巴州区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其下发的文件性质上也只是一般的行政管理文件,且不论其下发的文件内容根本不构成导致《合作办学协议书》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形,其性质也既不构成《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所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情形之第一项“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不可抗力”,也不构成第五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法律”。
三、Y中在X学校已经提起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过程中发出所谓单方解除合同的通知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X学校早在2017年10月26日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Y中支付当年使用费并支付违约金,其诉讼请求的本质,就是要求Y中按约继续履行合同。Y中却在诉讼过程中的2017年11月7日,向X学校发出所谓单方解除合同的通知,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对抗X学校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对于一方当事人已经提起诉讼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过程中,被起诉一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该通知是否能够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54号裁判案例早已作出明确的裁判意见,即“因司法权介入审查案涉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当事人已不能通过行使《合同法》中规定的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私力救济手段来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该通知行为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的该裁判案例虽然并非指导案例,但该案例现行有效(并未因审判监督程序而改判)具有既判力,对于本案认定Y中发出通知的行为是否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具有参考性。
【判决结果】
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除X学校和Y中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Y中向X学校支付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本学期)使用费共计900元。
【裁判文书】
关于《合作办学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以及是否出现法律、政策变化导致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X学校与Y中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签订于2015年,应受修订前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调整,该法并未作出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之规定。尽管在合同履行期间,国家法律发生了变化,但是根据查明的事实,依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国务院于2017年1月1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三点第九项的规定,结合《合作办学协议书》主要内容,《合作办学协议书》属于一般民事合同,不是商业经营行为,虽不符合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教育科技体育局制定的《关于深入推进名校引领办学的指导意见(暂行)》的相关规定,但该文件属于地方管理性规定,且该局对X学校和Y中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书》未作出任何认定和处理,《合作办学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Y中向X学校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Y中虽然在2017年11月7日向X学校及校长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已无法履行或不能按预定条件履行,要求解除合同,但时至今日,X学校现仍有Y中招收的学生上课,即双方实际上仍在继续履行《合作办学协议书》;且Y中向X学校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时间是在原一审程序之中,实为诉讼之举,故Y中反诉请求确认其与X学校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于2017年11月7日解除的主张与双方的实际行为相悖,其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合作办学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及何时解除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因双方对现行政策的理解不同,对合同是否应当继续履行产生根本性的争议,鉴于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已不宜继续履行,应当解除。Y中在X学校招收学校进行教学活动,实际使用了X学校的校舍、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应当支付使用费。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并且Y中向X学校支付2017年7月至2019年1月(本学期止)的使用费共计900万元。
【案例评析】
一、合同一方当事人作为违约方,即便出现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形,是否享有单方解除权?
《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所规定的解除权的行使,首先应当是当事人一方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基础上,根据法律规定或根据合同约定享有单方解除权。Y中在《合作办学协议书》的履行过程中,经巴州区教育主管部门(区教科局)调查确认,存在违规将X学校学籍学生安排至其校区就读、违规财务列支、违规使用账户等诸多损害合作利益、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但基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契约精神和诚实信用原则,不允许违约方反而因违约而获得利益,违约方无解除权应当是基本原则。如果违约方确实遭遇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形,其提出解除合同的前提,是其必须承担守约方因合同履行而可以实现的全部预期利益之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以换取对合同义务履行的免除。
二、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已经提起的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中通知对方解除合同,该通知行为是否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对于一方当事人已经提起诉讼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过程中,被起诉一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该通知是否能够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54号裁判案例已经作出明确的裁判意见,即“因司法权介入审查案涉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当事人已不能通过行使《合同法》中规定的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私力救济手段来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该通知行为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其理由在于,被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一方在诉讼过程中行使合同解除权,是为了对抗起诉方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在此情形下,若被起诉方行使解除权还能够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不但能通过此种解除合同的方式来达到其不承担违约责任的真实目的,还构成权利的滥用,违反《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该裁判案例虽然并非指导案例,但该案例现行有效(并未因审判监督程序而改判)具有既判力,对于本案认定Y中发出通知的行为是否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具有参考性,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第39条、40条的规定,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均应进行类案和关联案件的全面检索,以规范法院的裁判尺度和适用法律的情形。
【结语和建议】
合同解除之诉是民商事纠纷中极为常见的纠纷类型,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情形之一,签订合同的各方当事人通常也会将其作为合同约定解除的情形之一载明于合同中。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依据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一情形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因此,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主张基于“不可抗力”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能够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一是要看其主张的“不可抗力”是否真正构成法定或约定的“不可抗力”,二是要看其具体如何行使所谓的单方解除权。但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应当符合一定前提条件,也未对行使合同解除权的一方是否在任何时候行使合同解除权均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作出限制,在司法实践的进程中,希望能逐步统一裁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