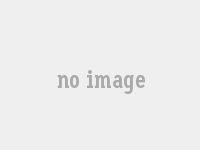律师受委托为余某盗掘古墓葬辩护案
- 案例时间:2017-12-25 00:00:00
- 浏览量:0
- 案例编号:JXLGLD1514187100DKEJ
- 案例类型:律师代理、辩护成功的诉讼案例
2015年5月份,马某某、刘某某、赵某某预谋到山东省淄博高新区四宝山办事处军屯村盗掘军屯汉墓,商定由赵树忠联系盗墓人。9月份,赵某某联系徐某,徐某负责出资并找人盗掘,并找到一直在老家福建打工的余某与宋某某等人,后约定了分赃比例。徐某出资租车,并购买绳子、铁铲、软梯、编织袋等作案工具。赵某某、马某某、刘某某、徐某、董某某、宋某某、汪某某、余某、叶某某在夜间多次对军屯汉墓进行挖掘。后因资金不足,叶某某联系李某,由李某出资继续盗掘古墓,在军屯汉墓内部横向挖洞十余米。2015年11月25日,当地村民(湖田镇北焦宋村)刘纪楼来此发现遗留下来的作案工具和新鲜的盗土,随即报警。淄博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四宝山派出所随即组织警力进行蹲守,并于11月27日3时许将负责望风的赵某某、马某某、刘某某抓获,经询问,三人对盗掘古墓的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其余同案犯的居住地点,同日8时许在青州市某某宾馆房间内抓获其余七人,其余七人对盗掘古墓的事实供认不讳。
对此,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余某等十人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对古墓葬造成了破坏,构成盗掘古墓葬罪的既遂,十名被告人构成该罪的共犯。
【代理意见】
(一)被告人余某所实施的挖掘古墓行为并没有对古墓造成实质损害,属于盗掘古墓罪的未遂。
从行为的危害性以及刑罚的目的来看,我国刑法之所以严厉打击盗掘古墓的行为,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埋藏在地下的珍贵文物和历史印记不受破坏。而本案中的行为,其一没有对古墓外观造成明显破坏,其二也没有触及墓壁,自然更谈不上损毁古墓内部结构和破坏珍贵文物,其三被告人余某等人通过盗墓也没有得到关于古墓年代、大小、深浅以及如何盗掘的有效信息。可见该行为的危害性较小,如若将其认定为盗掘古墓罪既遂,这显然扩大了刑法的处罚范围,有违刑罚的谦抑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包括水下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不以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为限。
实施盗掘行为,已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应当认定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既遂。
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以外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
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盗掘行为只有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才认定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既遂。
位于淄博高新区四宝山办事处军屯村的山东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军屯汉墓。从被告人余某等人所实施的行为结果来看,从2015年9月开始,先后陆陆续续对军屯汉墓淄博市高新区四宝山办事处进行盗掘,中间由于资金问题,被告人叶某某联系被告人李某,由被告人李某出资继续盗掘该古墓,在军屯汉墓内部横向挖洞,直至2015年11月27日,被告人余某等人被抓获时,也仅仅是对该军屯汉墓内部横向挖洞十余米。由于被告人实施的盗掘行为仅挖掘了垂直和横向盗洞即被发觉,并未触及古墓葬的文化层,尚未对古墓造成实质危害,也未损害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符合犯罪未遂的特点。
从罪刑相适应原则来看,如果将挖掘十余米盗洞的行为认定盗掘古墓葬罪既遂,那么在本案中,被告人余某的行为换来的将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相比较其他一些采取极大破坏性手段盗掘墓葬,损害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获得相同的刑罚而言,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二)被告人余某在进行的盗墓活动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从被告人余某参与犯罪的起因来看,是徐某先找了宋某某,后宋某某又找到了被告人余某,这说明余某并非本次盗墓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从被告人余某所实施行为的结果来看,其虽参与了盗墓活动,但是自己对如何盗墓也不懂,既没有盗墓经验也没有给古墓造成实质损害,只是一味地听从他人组织安排。从被告人李余某在几位同案犯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其既非策划者,也非投资者,更非组织者,其作用仅在于听从安排一味地挖盗洞。综合几点来看,辩护人认为余某在盗墓犯罪实施过程中也仅仅起到次要作用,属于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被告余某此前也从未受过任何处罚,平时表现良好,此次犯罪属于初犯,偶犯,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理。
(四)被告余某认罪态度诚恳,悔罪态度良好。
刑拘后,被告余某在看守所一直表现良好。在面对侦查机关讯问时也如实供述,积极配合。在庭审中也没有翻供或者供述不一致的现象,并能自愿认罪,可见其认罪态度之诚恳。另外,被告余某在辩护人面前也多次表达了其忏悔之心,在几次会见的过程中,每次提到他的家人,余某都忍不住落泪。余某肩负养家糊口的重担,为了家庭四处奔波赚钱,但苦于一直收入微薄,没有建树,如今却因一时贪念落得镣铐加身,失去自由,被告人对此悔恨不已,其发自内心的自责令辩护人感到惋惜和同情。被告人深知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理应受到责罚,但同时也更希望法律能够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一个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一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作为被告人余某的辩护律师,恳请法庭综合以上辩护意见,做出公正公平的裁决,给被告人余某一个知错能改的机会,相信他一定能好好反省,争取更好地回报社会。
【判决结果】
由于被告人实施的盗掘行为仅挖掘了垂直和横向盗洞即被发觉,并未触及古墓葬的文化层,尚未对古墓造成实质危害,也未损害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被告人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且为从犯。据此,淄博高新区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被告人余某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
【裁判文书】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某、马某、刘某、董某、李某、宋某、汪某、徐某、余某、叶某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成立。赵某、马某、刘某、董某、李某、宋某、汪某、徐某、余某、叶某盗掘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依法均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鉴于本案被告人虽然实施了盗掘行为,但仅挖掘了垂直和横向盗洞即被发觉,未触及古墓葬的文化层,尚未对古墓造成实质危害,亦未损害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某后期出资,被告人董某、宋某、汪某、余某、叶某具体实施盗掘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均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上述被告人归案后及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对其均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关于犯罪未遂、立功、坦白、从犯、认罪态度较好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余某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案例评析】
如何划分盗掘古墓葬罪的既遂与未遂,司法实践中,对此有着不少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窃得文物说。它认为犯罪未遂和既遂相区别的主要标准是犯罪分子所追求的危害结果发生与否。本罪中,犯罪分子所追求的危害结果是通过盗掘的行为盗取古墓中文物(葬品),只有其实施了挖掘行为并窃得葬品才为既遂。
二是破坏古墓葬说。持该观点的学者在具体表述上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行为人之盗掘行为致使古墓葬受到破坏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有的认为,构成本罪的既遂必须是整个古墓葬受到了严重破坏,否则,在已实施了盗掘行为的前提下即是未遂。
三是盗掘行为说。它认为,根据立法精神和司法保护的古墓葬这种对象本身所具有的不可再生的特殊性质,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掘古墓葬便构成既遂,而不能以盗掘行为造成古墓葬受到严重的毁坏结果作为既遂的条件。盗掘行为所造成的某种使古墓葬受到破坏的结果只能成为对犯罪分子裁量刑罚时所应考虑的情节。
从传统理论和司法实践上看,认为前两种观点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更多采纳的是该罪为行为犯。
首先就窃得文物说而言,其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有关犯罪既遂的理论来看。一般而言,犯罪的既遂(或称为犯罪的完成形态)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立足于犯罪人讲时,它就是指犯罪目的的彻底实现,而立足于法律讲时,则指某种犯罪行为已经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的要件的情形。我们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应该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而不能以犯罪人的自我认识为标准。否则,遗患无穷,极易为罪犯借口“目的未实现”来推卸罪责提供方便,这样,许多已经明显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恐怕永远只能是未遂了,从而也就使既遂未遂的认定失去了客观依据和存在的价值。显然,窃得文物说是从犯罪人出发理解犯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故不足取。二是从盗掘古墓葬罪的立法精神来看,它是为了更有效地防止古墓葬受到破坏,避免其中的文物流落他乡或遭到损毁。坚持窃得文物说就必然将那些挖掘了古墓葬而未得到其中文物(或者根本无法得到)的行为认定为未遂,这实际上是宽纵了犯罪分子,不利于对古墓葬及其中文物藏品的保护,不符合从重从严打击的宗旨,偏离了本罪的立法本意。
其次,就破坏古墓葬说来讲,其不足主要有:一是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所谓破坏,其本意为毁灭或损坏,也即使某种物品的使用价值全部丧失或部分丧失。但在认定具体的盗掘古墓葬案件中,这种本来明确的含义却可能变得含糊不清,难以把握,造成古墓葬面目全非、支离破碎,自然是受到了破坏,对此一般没有歧义。但是,由于古墓葬的种类、存在方式、外观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人对其遭受侵害所致的某种后果是否构成了对古墓葬的破坏就会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如仅将某古墓葬的封闭石门撬开尚未进入即被抓获的情况。由于它根本没有影响到该古墓葬的实际价值和内部构造,究竟是否属于破坏的范畴,即会形成认识上的分歧。至于何种情况下才可以称为“严重破坏”,更是难以形成一致的判断标准,从而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处理。二是不利于对古墓葬的保护。按照该说,对于那些对埋藏于地下的古墓葬实施挖掘行为但尚未直接接触到古墓葬本身,或者已触及古墓葬本身但尚未使之受到破坏的等情况,只能以未遂来处罚,这显然不足震慑犯罪分子,无助于对古墓葬的保护,实际上是失去了一道使之免遭破坏的法律屏障。另外,从刑法分则对本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来看,盗掘古墓葬罪是行为犯,而非结果犯。无论是从古墓葬中窃得文物,还是使古墓葬受到破坏,均不在其基本构成要件之列,再将之作为既遂的条件,加以限制,就超越了立法的内容,这也是此两说的缺陷之一。
【结语和建议】
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以及大部分学者的观点都认为盗掘古墓葬罪是行为犯,只要着手实施挖掘行为即构成既遂。本案的辩护难点也在于此。2015年10月1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63次会议、2015年11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也是此案的契机所在,盗掘古墓葬罪只有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才认定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既遂。
在现今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背景和舆论压力之下,承办律师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尽职调查、充分论证,最终获得了仅以犯罪未遂且属从犯来定罪量刑的辩护效果,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本所倡导的“尽心尽力、至专至精”的执业精神,更诠释了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作用。